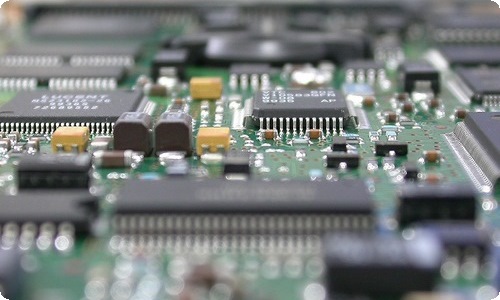冷与热
寂寥黑夜下的月霜,那是最寒冷的阳光。
深秋凄凉,清冷的月光稀释了乡村太过浓稠的夜色。厚重而古朴的黑漆大门内灶火灼灼,饭香阵阵,锅碗瓢盆交错的喧杂打破了老屋多年的沉寂。
姥姥矮小瘦削的身躯蜷坐在灶火前的小小板凳上,慈祥温暖的笑看平日精明干练母亲在锅前兴奋而骄傲的卖弄厨艺,眼神中是为人母的慈爱与自豪,时不时的往灶台下添把干草,使它发出一阵“噼啪”的爆破声,锅盖下钻出热气弥漫了整间老屋。蜷缩久了站起来捶打几下常年有病的腰椎,蹒跚着走进里屋看了看炕上姥爷熟睡的背影,似心安似无奈的摇了摇头。将那株不知名却绽放明媚的野花端进屋内,腐朽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呻吟,宛若岁月的叹息。姥姥的'脸上总漾着那和蔼温柔的笑意,对于那些年扼杀她如花青春的封建社会,那些年欺辱她的的地主恶仆全部予以大度的宽容。她的贤惠能干,有勇有谋十里八乡的人无不赞颂,她用枯瘦的双手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将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抚养长大,自我记事以来从她那里继承的便是宽容与善良,姥姥那和蔼的笑像那温柔的烛光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
氤氲的水汽中,神像前的那一对红烛盛在久远的已不知其年代的雕花烛台袅袅的燃着,温暖摇曳烛光似乎在诉说着姥姥的温柔与善良,那滴落的红泪被那古朴沉默的烛台稳稳接住,重新堆进那将要燃尽的蜡油中,使其得以生生不息。灶火渐熄,人们围坐在满桌佳肴前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所有光与影的变换在我睡意懵懂的意识中散落漫天繁花飞舞,这温馨闲适的光景与上一次相见恍若匆匆几世,让人喜悦的想要流泪,只愿时光定格不前。
皎月挂在舒朗的枝头,沉浸其中自得一份洒脱与清澈,风过处,卸下许多金桂的香气。我眯起眼睛打量着朦胧的寒月,伤感而害怕的想起那高楼大厦上惨白狰狞的白炽灯,宛如一张巨大而阴森的口,吞掉了悬在我童年的老屋的那盏昏黄的灯。
城市的空气一年四季都是生冷而粘稠,它无情而残酷的逼着人们,赶着人们平行的前进,好让这个世界得以冰冷的运转。每个人在晨光初现时便匆匆出门,钢筋铁板的高楼大厦像张着贪婪巨口的庞然大物,吞没着一批又一批被源源不断送入的人群。女人们总用精致的妆容掩饰内心的空洞,男人们总用翩翩的风度伪装入骨的疲惫。黄昏时人们低着头拖着行尸走肉般的身躯在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上缓慢推搡着前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麻木而冷漠的表情,仿佛全身的精力都被榨干。入夜后的城市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繁华喧杂的外衣下却有着无法言喻的冷漠与孤独。
老屋仿佛是与这个世界隔离的,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的风云变化它始终伴着那把姥爷常常在上面打瞌睡的老藤椅“嘎呦-嘎呦”的缓慢安然的前行。
这一方低矮,陈旧的老屋,是灵魂的安息地。这里有冷与热的分离也有交融。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纸迷金醉,只有脉脉红烛,悠悠夜色。
这里没有虚伪疲惫,奉承阿谀;只有闲适安逸,自在洒脱。
这里没有权势和名利,这里可以小憩和安息……